译者的几句话:
偶尔的机会,看到美国飞虎队历史学家福特在2008年出版的“飞虎队”一书,心想:此种书大概已经出了数百种了,过了60多年,居然还有人在写! 其中第五章的后半章,第98页-107页,讲到飞虎队成立以后的第一次空战:保卫昆明。这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以前的中英文书籍中,都是对此一带而过,从未有过详细的描述。这可是飞虎队的第一仗。打好了,士气大振。打输了,中国人民又要多遭日本人的轰炸。应该翻译出来供大家一阅,再有,我父亲生前多次提到当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逃空袭警报的事情。学生们上着、上着课,就听到警报声。什么也不顾,赶快逃出教室,到附近的小树林中避难。日本飞机耀武扬威,我们没有空军,高射炮打不高,更不够密集,没办法。还有XX 同学被轰炸死。而沈元(前北航院长)是个小个子,就近躲在一个土坑里,大个子进不去。类似的记载,在当年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录中,俯手可得。直到1941年12月,终于有了飞虎队,一仗打下来,日本人就再也没有来过了,(我父亲1942年夏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所以这段保卫昆明之战的翻译,就算是我对家父在天之灵的一点告慰吧。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表伯父(我父亲的大表哥)孙寒冰,在1940年重庆被日本人炸死,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
此书还记述的一件关于陈纳德的事情,在读此书之前,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飞虎队从一开始就把日本人打得找不着北,同样是美国飞行员,在此之前从未真枪实弹地面
对日本人的火炮。在当时的东南亚战场,包括菲律宾,就被已经身经百战的日本飞机员打的只有招架之力。答案之一是陈纳德在此之前的中国武汉保卫战中,仔细观察了苏联飞行员与日机战斗的过程。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发动机缺失强大的马力,所以其飞机的重量制造的非常单薄,以减少重量。好处是机翼载荷小,行动灵活,即所谓的“转弯半径小”,但经不住上下俯冲的加速压力,即所谓的几个G的飞行机动载荷。而美国飞机正相反,用的钢板厚,重量大,发动机马力大(类似今天的日本汽车和美国汽车之比较)。所以陈纳德要求飞虎队的飞行员,不要在同一个平面上和日机周旋,而是利用马力大的发动机,或向下的俯冲,或向上的仰攻。而日机结构不够结实,根本不敢做高速的上下运动,否则机翼可能在空中解体。 (我父亲在1952年北航建院时,曾亲自从北京南苑机场拉回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回北航做教学之用。就发现日机的材料薄的很,只有驾驶员座位后面有一块2寸厚的钢板,用来保护飞行员。)陈纳德的方法成功了,飞虎队旗开得胜。
第五章 开火,直到把他们打瘪为止
昆明远离缅甸的东吁(Toungoo) 1100千米,跨越了世界上最荒凉的疆界之一。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中国航空公司,当时因为美日并未公开宣战,所以飞虎队成员则是以中国航空公司雇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参战。中国航空公司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在1941年12月17日星期三,将飞虎队飞行员飞越高山,送到昆明,准备做战。第二天又有三架运输机,把指挥成员,以及足够二周做战的弹药,氧气和食物供应送到了昆明。
当飞虎队的战斧式战斗机离开缅甸仰光机场时,飞行员费里曼.里格特在滑行中撞上了一辆汽车。另一位飞行员乔治.博格特冲出了跑道。这样一来,只有34架战鹰飞到了中国。“熊猫”中队是分了二个阶断飞。中途在缅甸的腊戌加油,而“亚当夏娃”中队则是中途不停,利用仪表飞行,飞经腊戌上空,再转向东北方向,在6300米的高空飞越了山峦。
飞行员们很容易就从晴朗天空中的滚滚浓烟中找到昆明。几个小时之前,昆明刚刚遭到日机的轰炸。那是从越南河内起飞的日军第21中队的川崎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被美军戏称为“莉莉”的Ki-48,这些轰炸机是由中岛九七式单座战斗机护航。而这些战斗机则必须额外加装辅助油箱,才可以满足其1200千米的航程。飞行员费里兹.沃尔特写下了他第一眼看到被炸后的昆明:“我第一眼看上去就看到满街的瓦砾,被炸死、炸伤的人。中国人正在救护这些伤员,并且把尸体停放到干净的地方。”
飞虎队的司令部成员和“熊猫”中队的飞行员住在城北的:“第一旅馆”。二个人一个房间,床,桌,椅俱备。最麻烦的是取暖,只有木炭。不烧吧,寒气逼人。烧吧,又怕二氧化碳中毒。“亚当夏娃”中队住在机场路的“第二旅馆”。那的设施就有点原始了,甚至还是自制砖的建筑,被称之为:“土墙城”。
地勤人员就只能乘坐8辆卡车和2俩汽车,于12月20日从仰光机场出发到曼德拉,然后再到昆明。他们的车队运输了所有的重型设备,甚至也包括了禁运品。在二个星期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他们还必须和官气十足的英国人,献媚奉承的缅甸人,贪污腐败的中国官吏,还有当地山地部落的人。那儿女人的脖子上吊着装饰品,就象长颈鹿那样。无线电通讯员史密斯在“浪漫的皇家之路”中所描绘:我们驾驶在红土的公路上,道路俩旁长满了灌木丛,红色的尘土使得绿色的植被呈现出紫色的彩调。当我们驶过高山后,那儿没有了棕榈树。当地居民看起来更象中国人,而不象缅甸人。他们皮肤不那么黑了,他们穿着裤子,而不是裙子。
史密斯接着写道:昨天在我们下山的路上,要连续转十五个急转弯,才下到了一个水坝。中途我把车子停了下来,看看其它7辆车是怎样转弯的。 有的时候,那弯实在是太小了。司机只好向后倒车,再狠打方向盘,才可以挤过去。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如果稍微一不小心,多倒后几寸,那车子就会翻到几百尺的河流之中了。
东吁,被称之为A点,那儿还留下了以艾得—高以特为首的27个人。艾得原来是个飞行员,现在是个指挥官了。他们把那儿当做后方基地,为了维修,供给和做为昆明和仰光无线电通讯的中继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修那些因故障不能飞到昆明的几架战斧式飞机。
昆明被称之为X点,在那儿,陈纳德又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加入飞虎队的地面维修和后勤补给工作。美国海军借调少校罗伯特—迪沃尔夫为飞虎队的后勤指挥官。杰荷德—纽曼,一个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早在1939年就成为陈纳德的私人朋友,也加入了地面机械师的队伍。纽曼回忆到:这些地勤人员都是嗜洒如命的家伙,打扑克,粗野的个性。但他们却教会我美国式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加糖浆的烤饼或蛋饼。更没有见过棒球赛,而那些美国人称之为“女人气的德国人”。纽曼用他的手风琴来酬劳他的同伙,1941年的名曲:“当灯光再次闪亮时”。
飞虎队有4名飞行员在执勤,陈纳德认为日本人在星期四轰炸昆明时得了手,第二天他们还会再来。 但一直到星期六早晨9:30钟,通过前方的警报网,才得知10架日本轰炸机从越南河内机场,已经入侵了进入云南边境。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黄色的警告旗升了起来,陈纳德冲进了他的指挥部掩体,无线电报务员唐—惠普勒回忆当时的情景“在那阴湿黑暗的掩体里,陈纳德,他的翻译,无线电报务员,中国军人…….我从近处看着陈纳德的脸,随着中国警报网报告日本飞机的不断逼近,从电话中传出来的轰炸机的噪音越来越大,他的嘴紧紧地闭成一条线,手中握紧了从口袋中掏出来的烟斗,从他把烟丝装进烟斗的动作中,我可以看出他的紧张,数目不详的敌机越过华宁(译者注:在昆明南面偏东100千米)向西北方向飞来。”
几发红色的曳光弹腾空而起,16架战斧式战斗机从跑道尽头呼啸着冲上天空,这是“亚当和夏娃”中队的飞机。他们升高到4500米,转向东南,做为飞虎队进攻梯队,战斗机沿着铁路从昆明飞向宜良(译者注:大约离昆明南80千米,著名的“石林”即在此境内),在那儿截击了依靠仪表飞过来的日本轰炸机。飞行员之一的杰米—克劳斯写道他第一次做战的感受:“当你升到上面去时,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天空大的不得了, 真的是很容易失掉(敌人轰炸机的)目标,哪怕它仅仅就在你的前方一,二千米之外……上面很冷,我的挡风玻璃已经结了霜。”
第二“熊猫”中队作为预备队,4架战机在附近盘旋,另外4架也升到4500米的高空,10分钟之后,突然发现一个双发飞机的机队朝着他们飞来,(注:飞虎队的战斧战斗机都是单个发动机,简称“单发”。双发的飞机必是日本轰炸机)。日机离他们还有13千米,低于他们600米,排成“双V”型队列。前面4架排成菱形。后面是左右各3架,这是以河内为基地,日本陆军空军第21中队,在指挥掩体中,唐—惠普勒可以听到飞虎队飞行员的通话“他们来了”“这不是日机吧?”“还不是呢!你看看那(机身上)的红圆圈。”
日本机队队长富极正在做他惯常的袭击方法。 先在目标上空盘旋,然后突然接近目标。4架飞虎队“熊猫”中队的战斧战斗机突然从太阳的照射下冲了出来,甚至在还没有到达机头重机枪的射程时,就匆忙地开火了。日本的“莉莉”川崎久久式轰炸机匆忙丢掉炸弹,向东逃去。去掉了炸弹的日本飞机,几乎可以和美国战斗机飞的一样快。
正当日本富极带队向南逃跑时,桑迪—桑多正好看到它在5000米的高度上向他飞来。桑迪—桑多在他的战争报告中写道:“单立尾,铅制的机身,血红色的圆圈画在机身和机翼上,郁闷的灰色飞机。” 他命令2架“亚当和夏娃” 中队飞机在上空保护以防袭击,其余的4架成队列,每次2架从太阳的方向,向日机俯冲攻击。
按飞行员查尔斯—邦德的话讲,桑多可不是个优秀的指挥员,而仅仅是个“小家伙”. “留着小胡子,表情冷漠,在他的指挥中没有激情”。在战前的陈纳德操练的训练中,桑多总是从下方向上仰攻对方的飞机的腹部,也就是训练手册中飞机最容易被攻击的部位。而查尔斯—邦德总是从上方俯冲攻击对方。这时的日机,经过了飞虎队“熊猫”中队的第一轮攻击之后,只顾逃跑,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看到美国战斧战斗机时,日本轰炸机上的机尾射手才放下机尾的射击板,爬在上面,向后射击,但这样一来,日机的速度大大减缓。
这时邦德已经准备好了他的机枪,机翼上各二挺机枪,需要拉座椅两旁的下扣,而机头上重机枪,则是由在面前的控制板上发射。这时他就把瞄准器对准了日机,(以前飞机上的瞄准器是和普通枪支上的“三点成一线”一样,很难在空中瞄准。 飞虎队自己改制的瞄准器是由一面镜子来实现,详细原理可查)。
射击按钮是在操作杆上,邦德双手套着手套,紧紧地握住操纵杆,邦德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转动机身,开始俯冲,当最近的日本轰炸机到了射程之内,我猛按按钮。 他妈的,怎么什么也没有。我赶快检查射击保险。哈,我还没有把它打开!我只好重新把飞机拉起来,再俯冲下去,打开保险…..太妙了,所有的机枪都响了。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子弹射出去的弹迹。我射了一边又一遍…..眼看着子弹打进日机机身上……终于,2架日机落后,着火了,冒烟了。”(译者注:别忘了,这些美国飞行员实际上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做战,第一次把真正的子弹打进敌人的飞机,第一次真正的杀人。所有他们的“无经验”的错误,都可以、也应该被理解。)
在攻击队列中,另一名飞行员佛里兹—沃尔夫在事后对一家航空杂志的采访中讲道“我先从上面俯冲下来,冲过日机,再从下面向上攻击。在离日机450米的地方,我开始攻击。我都看见那个日本的机尾射手,我可以看到子弹子弹打进了他的身体,把他撕得粉碎……在相距100米的地方,我按了一个长射,把子弹通通地射入日机的发动机和油箱。一边机翼都快被打掉了…..爆炸了,日机在空中爆炸了。我赶紧把飞机转向。
之后,我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攻击的日机是V型队列中最外面的一架。我先俯冲下去,在和日机同等高度上拉平……我可以看到日机机尾射手在向我射击。哈,可就是没有一粒子弹打中我。…..近点,再近点。在50米的地方我开了火。日机爆炸了,这时我离日机太近了,只差几寸就撞上着火坠落的碎片了。
杰米—克劳斯亲自目睹了沃尔特的二次攻击。 他在给一本战时杂志写稿时写道:“那架日机就在我的眼前,我都可以看到机尾射手所戴的防护目镜的反光。就在我要按按钮开火的一刹那,他(沃尔夫)的子弹击中了日机。双方交火的子弹,在空中编织了一条条彩带。几十秒种之后,日机的发动机从机身上解体了。 我的飞机以每小时800千米的速度飞过。我的同伴正在把日机击落。”
预备队的领导是安德华—雷伯德,一个从前陆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的僚机是乔—罗斯特,一个矮胖的意大利裔的费城人,乔写道:“这场空战的飞机(美、日)看起来就像一群蜜蜂,如此密密的挤在一起。 我真怀疑他们为什么没有撞在一起。”这时雷伯德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乔写道“我随着队长向下俯冲。当接近最后面的日本轰炸机时,队长和我同时开了火。敌机上的碎片向我们飞来。当我们再拉起来时,看到日机只剩下6架了。队长的飞机又卷入到另一个圈子的战斗了。我实在挤不进去, 就只好在远处盘旋、待命。不过我敢肯定,那架日机一定是被击中了。
另一个飞行员是“熊猫“中队的爱迪—里克特。那个星期六应该是他轮休。但当他看到其它中队的飞机都飞上了天,他就按耐不住了。当时他的飞机正在做维修。但他不顾三七二十一, 先扯下机枪罩,又对地面维修人员大喊:“快,把驾驶舱盖上,我要飞了”。他戴上降落伞,爬上飞机,毫不耽搁打开发动机,滑跑,一口气地从跑道上腾空而起,几年后他回忆道:“我想追上大队,我的P-40是最好的。”他用的手来代表他的飞机的飞行姿态。“我看见8架日机在那儿,他们飞机像那样,我的飞机是这样。”
里克特还记得在缅甸学习陈纳德的射击技术。他这时到了一架日机“莉莉”的后面“…..我在他的正后方,面对那个混蛋的机尾射手,我锁定了目标,我眼看着我的子弹射中了他。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还不爆炸?目标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楚,大概是偏了几寸吧。 再次射击,拉起来,我终于看到火花了。但目标还在飞……我准备再次攻击他。慢慢地,日机头朝下,由火光伴随着,向下栽下去了。哈,全着火了。
接着,我又飞上去寻找目标。但我发现没有一挺机枪正常工作,怎样试,也没有子弹射出去,再检查,啊,枪管过热。没办法了,只好等它们凉下来。”
做为飞虎队的第一仗,美国飞行员报告有9架日本“莉莉”被击落。但最后确认的只有4架。2架是沃尔夫,1架是里克特,1架是米基. 迈克森。十二月二十日宜良的这第一场空战,是少数几次陈纳德的地面观察站和日本的记录相一致的,而和飞行员的报告相差很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V型机队右侧3架飞机,被多次地攻击,或者说整个空战中美国飞行员都在进攻日本机队的右侧。3架日机都被击落。这3架飞机的发动机都从机身上解脱了。从空中看来,无数的碎片在乱舞,美国战机是数架一起地攻击一架日机。在战火硝烟中,那时人的肾上腺激素膨胀,括约肌抽搐,全部视觉都集中在冒烟和着火上,目不转盯,对于其它的事茫茫无知,每个飞行员都做了俯冲,都开了火,都看见敌机冒烟和起火,那当然是自己射下来的。
只有飞行员鲍勃—尼尔是冷静的。20年之后,在1962年当他被问及在那天是否也打掉日本机,尼尔回答说:“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打中了一架日机。没错,你可以看见日机,但看见可比射中容易多了。….战场实战对我是第一次。我可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成为英雄的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奢望过。
一个中国地面站,在美国战机退出战斗之后,接收到7架日机的通话,这就旁证了日本人的计算。毫无疑问,日本人遭到重创。一个日本飞行员在1992回忆到:“战斗持续了大约30分钟,在它结束之前,坐在我后面的机尾射手就死了,我左边的那位也死了。但我们飞机上的油箱都是用橡皮密封的,既使中了子弹,也不会起火,所以我们有7架飞机得以返航。但某些飞机不能放下起落架,有的用单个起落架,有的是用机腹着陆。每架飞机都带伤,我的飞机就有30个弹孔。
几天之后,中国报告第四架日机在河内降落之前在空中爆炸。美军飞行员们决定大家共同享有这份战果,14位“亚当夏娃”中队的飞行员,加上“熊猫”中队的爱迪—克里特,每个飞行员得15分之4的战绩(译者注:原文如此,但应该为15分之1的战绩)。
日本历史学家同意日本在空战中损失了3架,在河内以外的空中又损失了一架(正符合中国的报告),另外7架严重受损,14个空中机组人员死亡。这是日本入侵东南亚以来最惨重的伤亡。在此之前,陈纳德就说过:如果日机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力量,它们就不敢再来了。陈纳德的预料没错。日本的第21中队再也没有来这个伤心地——昆明了。
美国飞虎队的损失是一架战斧式战斗机。在返回(昆明)巫家坝机场时,爱迪—里克特在飞机没有燃油的情况下,他采用机腹着地的迫降方式,把战机降落在一块菜地里。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把机枪和弹药夹从飞机上拆下来。然后在附近的一个飞虎队观察哨的掩体里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搭上一辆中国军队的便车,带着拆下来的机枪,安全地回到了昆明。
昆明人民在遭受日机的轰炸一年之后(译者注:也包括我父亲),第一次经历了胜利的喜悦,他们冲向飞虎队的机场,欣喜若狂。乔—罗斯特回忆道:那次庆祝胜利“我们先是听到乐队的奏曲声,接着大群的人就出现在进口处。市长在前面,成千上万的人都跟在他的后面,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什么东西来表示谢意。当市长发表讲话时,我们都站成一排在听着他讲……有着漂亮面孔的天使般小女孩们,站到我们的对面,把长长的丝带和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手腕上也是花带。”
陈纳德却不以为然,把此次战斗成为“毫无经验猎手的冲动”。他对于一下子就冲进日本机队、而未能保持自己的编队,因此而陷入混战大为光火。尤其是对桑迪. 桑多,无线电报务员唐—惠普勒回忆:“那个老头子(译者注:飞虎队员私下里对陈纳德的戏称)看上去怒发冲冠,但他终于没有说出口…..他让飞行员们坐下来,就象一位慈父一样,一一讲解他们的错误。最后,他说到:“伙计们,下一次要把日本人全部留下来。”
因为时间差的关系,美国各家报纸都在12月21日,第二天发表了这次空战。在全球战争的大范围里,云南的这场空战不过是“小儿科”而已。所以“纽约时报”仅仅把它放在第27页上。而“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却看到了此空战的不平凡之处。做为一个超精明的新闻记者,卢斯出生在中国。在1914年5月访问中国时,就看到了中国战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卢斯在中国访问期间的陪同是泰迪—怀特,是一个在重庆和陈纳德同一个卫理公会教堂的伙伴,和陈纳德吃喝不分。当卢斯返回纽约时,就把怀特带回美国做为“时代周刊”东亚版的主编。这可是一个美妙的组合,智慧,动机和动人的故事。怀特清楚飞虎队每一个人的背景,卢斯正想把此事做大。于是俩个人就此一拍而合,推出了一个感人的大标题。
故事的标题“血色飞虎队”。它叙述到日本飞机是怎样在3年内无情地轰炸不幸的中国人民,死伤无数。一直到由冷酷,沉默寡言的陈纳德上校组建了这支美国飞行员的义勇军,来到了亚洲。” 上个星期,10架日本轰炸机又耀武扬威地来到云南,目标是滇缅公路的终点:昆明。日军以为又是去轰炸一个不设防的地市,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哪想到,在昆明南面50千米的地方,飞虎队猝然发起进攻,把日本人打懵了。4架日机冒着火载到地面。其余的掉转了屁股逃跑而去。飞虎队的伤亡:无一伤亡!
飞虎队,多么响亮的名字。在飞虎队刚刚招集时,中国战时指挥部要求美国迪斯尼工作室为美国志愿飞行队设计一个标志。最后这个“长着翅膀的飞天老虎”就成了飞虎队的队标。泰迪—怀特就把它用在了“时代周刊”上,流芳至今。(译者注:另一个说法,飞虎队P-40飞机画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而中国内地居民没有见过鲨鱼,就误认为是老虎头,于是中文的“飞虎队”名称在前,英文名称在后。战机是鲨鱼在前,队标的“老虎”在后,由此可证。)
此文章是笔者很多年前翻译的。最近把此文发在一个微信群,西南联大家属群。当时有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回复的微信,证实我所说的。他的微信:飞虎队战机上下穿越日军机队。他是1934年出生,当时7岁,已经是小学生了,记忆犹新,可信度没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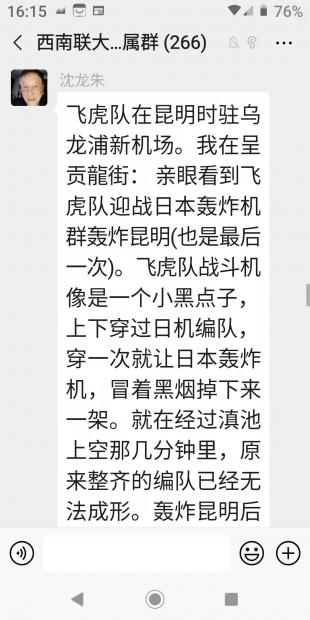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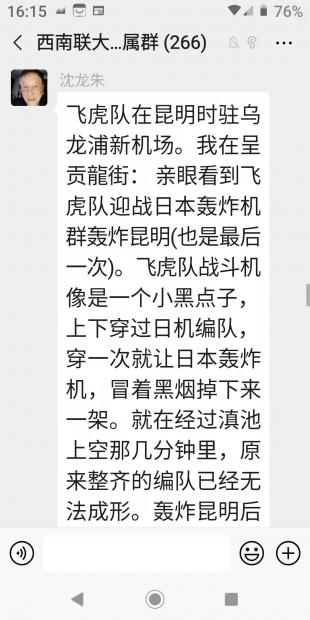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